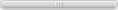[大视野]一个剧团背后的桐城文脉 ——桐城市黄梅戏剧团转身八年掠影
当天未组织演出的其他票友悄悄地跟记者说:“其实我们比他们唱得更好。”
车辆从郊区开向城市,那种浩浩荡荡的场面,让不少孩子兴奋得狂呼乱叫。

《胭脂湖》剧照
1935年11月13日,天津。
一声清脆的枪声响彻佛堂,漫天飞舞的传单在混乱的人群中洒落。
在人群中,一名女子镇定地站在那里,等候警察到来。洒落在人群中的《告国人书》上写道: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与传单附在一起的,是一幅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那是施剑翘父亲的遗照。
当天,京津各报纷纷发出“号外”,次日宁沪各地也以“血溅佛堂”为题爆出这一特大消息。桐城女杰施剑翘刺杀军阀孙传芳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
2012年5月,在施剑翘的家乡安徽桐城,以“刺孙”案为题材的新编黄梅戏《惊天一兰》正式定稿。这部由著名剧作家侯露编剧、黄梅戏作曲家陈精耕谱曲的剧目,是桐城市黄梅戏剧团自2006年创排《胭脂湖》、2007年创排《桐城六尺巷》之后的又一盛举。
对黄梅戏来说,此举无疑引人注目。作为黄梅大师严凤英的家乡,桐城人的自信更在于诞生了大名鼎鼎的桐城派。在传统耕读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的交融中,当地的黄梅戏也显出了别具一格的特点。这是桐城人努力打造的一个文化标识。
“在桐城市黄梅戏剧团经历转企改制、创排多部颇具当地文化特色的剧目之后,桐城人的文化精气神在哪里?桐城黄梅戏的性格是什么?”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炜透露,这也是此次创排新编黄梅戏《惊天一兰》的立意所在。
>> 说不尽的桐城往事
在民国时,“刺孙”案曾震动全国,但施剑翘这个人物“入戏”黄梅依然让人意外。一直以来,黄梅戏多以淳朴流畅、明快抒情见长,生活气息浓郁。这种风格特点,跟“刺孙”案所代表的激烈尖锐的冲突和铿锵侠气相比,似乎大相径庭。
“黄梅戏其实是一种很宽容的剧种,它有很多传统的才子佳人戏,也可以唱田间劳动、百姓生活,唱天仙神话。黄梅戏是我国的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应该摆脱小戏小曲的概念,在新题材、新内容上有新的拓展。”在侯露看来,这种拓展的背后,实际上包蕴着一个剧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求变思通,“它还应该能够唱激烈尖锐、声腔豪迈的戏”。
宽亮的落地窗外,雨越下越急。发生在77年前的那段传奇往事,显然让侯露的内心并不平静。她生性豪迈,酒量奇好,十分健谈,尤其是骨子里就有一种侠客情结。更关键的是,回望那段并未如烟的往事,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座小城的性格。
几百年前,以姚鼐、方苞、刘大櫆等为代表的安徽桐城派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势力渐张,其文脉流传更是臻至民国。“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宰相张英“让墙三尺”的故事,在桐城家喻户晓,桐城六尺巷也和文庙一起成为当地著名的文化景点。桐城市黄梅戏剧团创排的《桐城六尺巷》即取材于此。
“我们坚持每年复排新剧目两到三台,以丰富的剧目适应黄梅戏演出市场的需要。”桐城市黄梅戏剧团团长龙章才的语气十分诚恳。在宰相张英让墙三尺的典故、黄梅大师严凤英的人生传奇之后,桐城有说不尽的往事,剧目创作并不缺乏题材。
选择“刺孙”案为题材创作黄梅戏,涉事复杂,也有很多疑点。说不尽的桐城往事,在这里透出了一种形与神的纠结,却蕴藏着突破的契机。戏中透出的那股侠气,那种从家仇到为国除奸的境界提升,对黄梅戏实属罕见。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周育德指出:“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题材剧。”而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爱国也说得很严肃:“我们排这样一出戏,目的不是一定要获奖,而是要通过这样的举措,把桐城作为‘文都’的精气神提升起来,把桐城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精神面貌充分地展示出去。”
事实上,这也是侯露陷入沉思的重要原因。一座文脉昌盛、孕育了大名鼎鼎的桐城派的小城,一片诞生了黄梅大师严凤英的土地,“以戏播文”、“以文育戏”成为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时代命题。它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剧团在转企改制后的生存选择,更是一个剧种在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民间戏曲氛围的土地上的自我定位问题。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