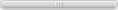又见那美丽而纯粹的民谣——记“新民歌运动”发起者、新疆歌手洪启

开朗的洪启认为新民歌每天都在进步
新民歌运动的旗手
1993年,洪启在歌曲《红雪莲》中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有一天你上了天山再也没有回家来,在冰雪过后我找到了你那冻僵的身怀,你的怀中放着为我病中所采下的红雪莲,我知道这是你对我最后的表白。”当时这位只有20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却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19年后的今天,洪启已经从少不更事的音乐爱好者成长为“新民歌运动”的发起者和标志性人物,被一些媒体称作“中国民谣界的切·格瓦拉”,而他的作品也被盛赞为“中国流行音乐中罕见的美丽纯粹民谣”。6月7日,洪启开启了一场名为“歌声中流浪的孩子”的活动,他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音乐,帮助那些漂泊在中国大江南北的新疆流浪儿童重返家乡。
洪启至今仍然记得1994年自己在乌鲁木齐西北路街头的一个站台上看到的那张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印着一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小男孩的头像,照片下面是孩子父亲写下的一行歪歪扭扭的文字:“阿里木江,你在哪里?”那个走失的维吾尔族男孩的眼神触痛了洪启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也促使他创作了自己最为著名的一首歌曲——《阿里木江,你在哪里》:“阿里木江是个孩子他迷失在了街上,他的父亲从此脸上再没了欢畅。阿里木江在那一天他迷失了方向,他的母亲的心永远和他一起流浪。”
从歌词、旋律到配乐、演唱,《阿里木江,你在哪里》都堪称洪启新民歌理念的集大成者。“所谓新民歌,就是一种与当下流俗化甚至油俗化的流行音乐泾渭分明的音乐形式,新民歌传达的应该是一种温暖的声音,它会以一种简单而质朴的方式来反映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心声。”洪启说。
“尽一切可能反映时代与人民的心声”,洪启的音乐观念就是如此简单。如果说出生于新疆的洪启在音乐形式上的老师是王洛宾、雷振邦、石夫,以及无数美妙新疆民谣的创作者,那么在音乐观念方面,他的启蒙者可追溯至伍迪·格斯里、鲍勃·迪伦、比奥莱塔、李双泽、胡德夫,而他最重要的精神导师,则是曾经的吟唱诗人、如今的戏剧导演张广天。
1993年,洪启离开故乡新疆,辗转来到北京,住进当时名闻京城的圆明园艺术家村。在那个先锋气息浓厚的艺术村里,洪启遇到了年长自己7岁的张广天。彼时的张广天,已经出版了中国现代民歌的发轫之作《张广天现代歌曲集》,并提出了“民族音乐现代化”的口号以及“汉藏和声”的概念,正是在其强大气场的影响下,洪启正式踏上了民歌创作之路。
4年后的1997年,洪启创作的《红雪莲》通过电台传遍了新疆的大街小巷,这首干净而纯粹的情歌至今仍在被人翻唱;8年后的2001年,洪启在新疆大学礼堂举办了“新疆新民歌高校巡回——洪启作品演唱会”,首次将新民歌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性的运动。“我们的新民歌,不是老歌新唱或者对优秀民歌的改头换面,而是要在音乐形式上不拘一格,传承优秀民歌真切反映人们生活、情感的精神,创造出更好、更贴切的反映、表现这个时代现象与状态的通俗而不庸俗的作品。”洪启当时曾如此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歌理念。
正如1975年杨弦在台北举办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成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洪启2001年在新疆大学举办的这场演唱会也标志着“新民歌运动”的全面展开。在随后的11年中,小娟、李净禅、野农、何力等歌手先后投入了“新民歌运动”的怀抱,而运动的发起者洪启则接连出版了《红雪莲》《阿里木江,你在哪里》《九棵树》《谁的羊》4张个人专辑,“新民歌”三个字正在从悄无声息变得愈发掷地有声。
理想主义的诗人
回顾起“新民歌运动”11年的发展历史,天生拥有维吾尔族开朗性格的洪启总是说,新民歌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现在‘新民歌运动’发出的声音还没那么响亮,但与几年前相比已经强出太多。搞民歌运动应该是一生一世的,时代越发展,年轻的听众对民歌越漠视,我们就越有这责任让民歌更具生命力。”洪启说。
新民歌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洪启说来自民间,更来自当下这个时代。“我自小生活在新疆,那里是民间歌谣的海洋,歌谣形态丰富,数量庞杂,生活气息浓郁。民歌的魅力无处不在,其中蕴含的深刻力量,绝不是那些流行音乐的小伤感、小情绪所能比拟的。”洪启说,“我们在创作新民歌的过程中,还是在宣扬传统民歌、使用传统乐器,那么新民歌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将鲍勃·迪伦、李双泽、王洛宾的精神与当代社会相融合,在传统的音乐形式中填入新的内容,就是新民歌的生命力之所在。”
在歌曲《回乡之路》中,洪启就通过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旋律与和弦,吟唱出了如今的人们对于故乡的情感:“请允许我把你的故乡,也当作我的故乡。请允许我把你的闺房、葡萄藤和月亮,也当作我的天堂。”在离乡背井已成为国人生活常态的今天,这样的歌曲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显得尤为可贵。“每个人都有思乡情结,但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对故乡的情感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洪启说,“就以我为例,刚到北京那会儿,我每次回到乌鲁木齐,都会嗅到一股亲切的家乡气息。然而19年过去了,新疆正在离我越来越遥远,它已渐渐成为我的一种留恋;相反,北京的气息却让我感到愈发熟悉。我怀念大西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能永远也回不去了。正如王洛宾先生是个北京人,但去了大西北,再没有回来。”
洪启对于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他的创作始终富含养分。“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式化,有人担心民歌创作会就此走向枯竭,但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洪启说,“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经历着与前人大致相同的事情,写书的人依旧写书,卖豆腐的人仍然卖豆腐,思乡的人继续思乡。只要生活还在继续,民歌的创作就会继续。”
然而飞速变化的时代,也的确有时会让洪启感觉自己的脚步太过缓慢。在歌曲《雷锋日记》里,他唱道:“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生活的岗位上?”而在歌曲《红旗谣》里,他则唱道:“唱的是什么?唱的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是正义和公正。哪儿有真理?真理在山岗。有一面红旗,在那儿飘扬。”如此充满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的歌词与简单优美的旋律相叠加,甚至会让听者怀疑这是两首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歌曲。
洪启不否认自己对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饱含感情,他甚至有一首歌曲就叫做《革命时期的爱情》。“我们这代人大多具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童年时期的那些红色记忆,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然而当我踏上创作之路的时候,却发现社会的变化之快超乎我的想象,比如我年少时梦寐以求的磁带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就连CD都被数字音乐打得节节败退。”洪启说,“既然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时代,那么干脆就落后一点儿,通过一种看似‘陈旧’的形式把自己的心中所想清晰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创作方式。我相信雷锋是一个纯粹、理想化的人,因为做一个好人、做几件好事,终归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在歌曲《雷锋日记》的意境中,雷锋的形象是永远成立的,这对于我而言就足够了。”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