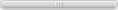只有进步才能赎回尊严 ——观香港电影《浮城大亨》
香港电影新浪潮一辈蛰伏多时,近几年可说是进入了爆发期。前年有罗启锐、张婉婷夫妇的《岁月神偷》,今春有许鞍华的《桃姐》,严浩的《浮城大亨》也在近期登陆,虽没有前两作影响大,影院排期也很有限,但论片子的质量,可有一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带有浓重香港本土特色的文艺派导演,在新世纪的创作中,不约而同回望香港历史,以本土化的平民视角,重新审视这座在近代历史中饱经沧桑的城市,在反思历史和现实之余,流露出浓浓的怀旧情调。也许对于许鞍华、严浩们而言,无论功过祸福,城毕竟是他们的城,或说是他们的家。随着他们渐入暮年,试验的冲劲已然被回忆的欲望取代,摄影机成了凝聚记忆的时光机。
《浮城大亨》是一个工整的文本,难得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能够贴切地成为一座城市的寓言。主人公布华泉的人生轨迹与香港城市的命运如出一辙,片名中的“浮城”既是主人公儿时漂泊海上的渔船也是香港这一浮动在东西方文明板块缝隙中的城市的代称。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的“香港人”在一次次震荡中,身份认同不再是坚实的,而是同样处于浮动状态。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恰恰譬喻了“香港人”在殖民主义的环境下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
全球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相伴而生,本片的题材决定了作者必须处理殖民主义的问题,并正视其复杂性。
严浩站在香港本土的立场,避开了一边倒式的批判或肯定,殖民主义带来了压迫和不平等,但不可否认,也促使香港成为亚洲现代化的先行地域,用资本主义的商业准则淘汰了传统中封建、落后的部分。帝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有种族歧视色彩,但毕竟用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高效率的现代科层制取代了生产性低下、充满封建色彩的船东制度,布华泉得以跳出穷途末路的传统环境、实现阶层跃升,正是托现代科层制之福。
与西方相关联的元素有提供慈善和知识的教会、重视个人能力胜过出身的老板、较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等等。西方的负面色彩体现为种族主义,如那个将“half breed”(半血统)之名强加给布华泉的英国上司、拒绝布作为英国国籍者排队查验护照的海关职员等等。对于种族主义者的羞辱或刁难,布一直试图进行抵抗和解决,虽然偶尔不得不因现实功利而屈从。
再看东方,与布在公司凭个人能力晋升的顺利正相反,母亲多次参加船主执照考试,却因拒绝向监考官行贿而不予通过;与西方教会及牧师对孤儿寡母的救助正相反,船东变本加厉盘剥布华泉一家……通过种种对比,中式传统社会作为一个“礼俗社会”与西方式的“法理社会”相对立,而后者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白人种族主义带来的屈辱感,是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副产品,即便如此,现代化之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融入现代体制,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改变,这正是布华泉成为帝国东印度公司首个华人大班的意义所在。
本片的态度符合香港本土的历史观念,对于殖民主义的后果有较为理性并契合具体历史语境的认知,“丧失自我尊严”是“现代化进步”的代价,然而只有“进步”了,才有可能重新赎回失去的尊严。
虽然跻身西方化的上流社会,但在布华泉心目中始终保留着对于前现代自然文明的眷恋情怀,他尽管时常陷入困惑,好在依然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主人公对传统的归属感通过他身边的女性角色传达出来,妻子阿娣某种程度上是早夭的小表妹的代替品,即便被代表西方价值的职业女性菲安吸引,布华泉仍然守住了传统的婚姻伦理。片尾他对阿娣唱起疍家人古老的求亲歌谣——童年时他与小表妹曾天真对唱过,他宣示了重拾传统的姿态,这发生在他全面完成“西化”之后。回望传统,说明此时的他开始对昔日渴望的“天堂”——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在“模仿”之后,“反思”是建立独立的主体性身份的必要步骤,不经这一步,将永远作为西方的赝品被轻视,永远不知道“我是谁”。
最终,布华泉回到了他人生开启的地方,获知了生母/中国的悲惨遭遇,他对于生母的遭遇未尝不同情,但他心中已然把养母/香港当做真正的母亲,给养母带上了那枚标志着“母亲”身份的耳环。这也透露出本片对“中国人”和“香港人”这两种相联又相异的身份认同的态度。至此“我是谁”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浮动”不再是痛苦的来源,相反,正是“浮动”构成了主人公/香港独特的身份认同,最终带来的是文化自信。有趣的是,完成了现代化的香港转观现代化刚刚起步的祖国内地时,仿佛看到了昔日那个缺乏文化自信、急于模仿的自己。布华泉与操着浓重东北口音的内地游客用英文对话,这个场景的意味不言而喻。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