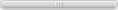对民族历史艰难的自省——观话剧《雾蒙山》
◎ 这部剧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对题材的敏锐捕捉,更在于题旨的深化,提出了只有致力于人的精神价值的提升,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进程这一时代课题,具有普适性价值,能引发当代人对人类心灵本质的重新审视。
◎ 透过显露的叙事层面,经由矛盾冲突、戏剧结构、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等感性认知与审美体验的牵引,观众的思绪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到理性思考的潜隐层面,进入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民族历史自省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进入到人文关怀、历史感悟和文化反思的深层空间。

话剧《雾蒙山》剧照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河北省承德话剧团上演了河北省著名剧作家孙德民编剧的新作《雾蒙山》。这部作品对历史变迁中新一代农民精神层面的追求有敏锐的感知与发现,表达了创作者对我国广袤农村人口众多的农民群体情感、理想和期盼的殷殷关切。同时,这部作品又是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上,面对20世纪中期那段令人心碎的民族劫难的历史自省和反思。
《雾蒙山》讲述的是一个精神领域里“父债子还”的传奇故事。大幕开启,雾蒙山老村支书张松病亡入土时,积怨甚重的一伙村民们扬言:张春山要是不代他爹赔礼道歉、磕头认错就要“截灵”。舞台上两伙村民“起灵”和“截灵”对峙,这一剑拔弩张的戏剧情势迅即地把尖锐的戏剧冲突赫然推到了观众面前。这部作品中儿子要替父辈偿还的,是十余年来一直纠结在村民心头的那一笔一笔“人情债”,这是情感上的还债,精神上的还债,是抚慰心灵的还债!
实际上,生活原型中的张松父子两代人已颇具戏剧性。“文革”前张松曾担任雾蒙山老村支书,在极“左”思潮雾霾笼罩的小山村,在“阶级斗争天天讲”,“上纲上线”无处不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年月里,他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不自觉地推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让不少村民们内心和情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也因此张松与老村长韩东、村民赵大有等结下了恩恩怨怨并殃及其亲属。然而十余年后,村民们对张松一家人的态度却有了截然转变。张松之子张春山不仅被村民一致推选为雾蒙山年轻的支部书记,而且在村子里威望极高。这事有点蹊跷,引发了孙德民极大的创作冲动。他紧紧抓住这一题材悉心地捕捉、发现与开掘。他以老一辈知识分子特有的赤忱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笔端流淌出的人物与事件倾注了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也渗入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感悟和深邃的文化思考。他力求让作品向哲理思辨的境界提升,以此引领当代人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弯路进行自省,对剧中人物的戏剧行动做出更加符合当下社会心理的、更具当代意识的价值判断。
谁能说,在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老支书张松不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带领雾蒙山的乡亲们修建四百亩大寨田,“战天斗地夺高产”豪情万丈;他当了一辈子农村基层干部,连公家的一个米粒、一根秫秸都没沾,临死前连自己看病抓药的钱还是从信用社贷的款;他“割资本主义尾巴”,猛批进城打工赚点零花钱的村民赵大有;他将一直与自己搭档的老村长韩东在高粱地里与富农女儿搞对象说成是“蜕化变质”,绝不留情地狠狠批斗,弄得韩东威风扫地从此在村里抬不起头;他“上纲上线”,把地主出身的赵华与儿子春山恋爱说成是“别有用心”,是要“把贫下中农子女拖下水”,因而粗暴地割断了这对年轻人美好的爱情;他为了表现自己以身作则、思想觉悟高,绝不让人说闲话,生生断送了亲生闺女青妹上大学、招工等锦绣前程,招致青妹受不了一次次残酷打击落下了精神残疾。张松的所作所为我们并不陌生,张松犯下的错绝不属于道德品质恶劣。他是这样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这样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为何在这小小的山村中却“洒向人间都是怨”?
我们看到,张松的为人诟病、为人唾骂、为人诅咒,似乎在于他不够通情达理,在于他“不食人间烟火”,但刨根究底其实质全在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犯的错不是他一人的错,是忠诚地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路线造成的错,是那个时代所推行的错误的思想方法、错误的思维方式造成的错,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犯下的错。其实,张松自身又何尝不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呢?
“父债子还?”“这不公平!”“历史的错能让我爹一人背吗?”在剧中我们看到,血气方刚的张春山一开头也咽不下这口恶气,他一咬牙,一跺脚,进城去闯荡天下了。这一走就是十年。然而亲情终究割不断,他毕竟是在雾蒙山长大的,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他都是那么亲切亲近,他怎能忘却雾蒙山对他的哺育之恩?
张春山在山外闯荡的这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雾蒙山在春山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他无时无刻不牵挂。雾蒙山的乡亲们还没有走出极“左”思潮伤害下的心理阴影,至今仍沉溺于恩怨情仇的折磨中不能自拔……张春山不能无视这一切,他必须勇敢地面对过去,面对历史的过错,面对历史已经翻过的这一页。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在城里的生活,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雾蒙山。
“春风地气通”“人和天地宽”。年轻的村支书张春山感受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前景的召唤,他要像他爹当年一样担当起领头羊的重任;他要抓住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机遇大展宏图,帮助乡亲们彻底改变山村的贫困旧貌,带领全村人走向共同致富的道路;他规划着要在雾蒙山建起板栗园和果品加工厂,还要组织富余劳力进城务工让人人的腰包都鼓起来;他不计家族恩怨,掏心窝子地挨家挨户寻访,替他爹赔礼道歉也反省自己曾经的过错和迷茫;他忍辱负重、以德报怨地劝说村民们忘记过去的恩怨,走出历史的阴影,跨过心头这道坎儿;他推心置腹地确认村里那些心灵受伤者的人生价值,使他们重拾生命的尊严。终于,张春山以他的真诚、阳光和磊落融化了村民们心底的仇恨,那些曾经要“截灵”的人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终于被打动,他们不再搅局,与春山一家冰释前嫌。村子里人与人之间那些几乎越系越紧的死结终于被松动、被解开,儿子终于偿还清父亲当年欠下的这些“人情债”。剧中的张春山志存高远、胸襟坦荡,他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直面现实,更敢于直面过去。他具有超越前辈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格,从这一人物形象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在这急剧变革的年代里,新一代农民已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
这部剧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对题材的敏锐捕捉,更在于题旨的深化,提出了只有致力于人的精神价值的提升,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进程这一时代课题。话剧《雾蒙山》的题旨具有普适性价值,能引发当代人对人类心灵本质的重新审视。在叙事层面,剧作家已把饱蘸人文关怀的笔触探入曾经深受极“左”思潮伤害的一代农民兄弟心灵深处,试图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心去消弭极“左”路线带给农民群体的恩恩怨怨,去抚平他们心底难以愈合的创伤。同时我们感悟到,作品在不经意间已触碰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潜藏,触碰到极“左”思潮肆虐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似乎已成为深深横亘在整个民族心底的那道伤痕。但它与“文革”后曾经一度涌现的“伤痕文学”又有不同。《雾蒙山》并不耽恋于村民们疗伤的悲悲切切、怨天尤人,更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你召唤,它鼓舞着已步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人们向前看、莫彷徨,洗刷掉历史旧账的污渍,携手和谐共进,意气风发地开创未来!从一代新人张春山果敢的作为和他高远的精神境界,我们分明看到了时代在前进。
应该说,胡宗琪导演在二度创作中为这部现实题材剧作确立的舞台形式感是恰切的。舞台景观呈现出层层叠叠的大山深处,几座低矮、狭窄的小房子的视觉形象,直观地传递出长久以来压在村民们心底的憋屈和纠结;舞台调度采取一群一群村民们不时地在写意的空间里跳进跳出地窥视,忽而冷眼旁观忽而介入剧情表达应有的情绪反应,在写实与写意的纵横交错之间,这种独特的群众场面的不断反衬与烘托,构成了这部剧作独有的假定性,意味深长,耐人咀嚼;第七场,已故老支书张松墓碑前,韩东向老搭档敬酒唠嗑时张松灵魂的出现,及整场戏中张松与自己的亲人和村民们的超时空对话,打破了现实主义风格作品表现手法的单一,为这部剧作的舞台呈现涂上了一抹诗意,让台上台下的心灵呼应伴随着戏剧节奏起落更有韵律感。透过显露的叙事层面,经由矛盾冲突、戏剧结构、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等感性认知与审美体验的牵引,观众的思绪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到理性思考的潜隐层面,进入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民族历史自省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进入到人文关怀、历史感悟和文化反思的深层空间。
在重温《讲话》的时日里,承德话剧团奉献出这样一部优秀剧作,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头活水。该团数十年来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得到了生活的滋养与馈赠。
(编辑:孙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