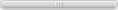个性化才能多样化
6月6日晚,众多音乐家聚集在北京音乐厅,作曲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登台宣布,经推荐、评比等诸环节,12首社会广为传播并认可且专业性可听性兼备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合奏作品从百余首作品中胜出,成为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与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新绎杯中国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合奏作品)评奖”的获奖作品。彭修文的《秦·兵马俑》和刘文金的《长城随想》荣获特别创作奖;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谭盾的《西北组曲》、金湘的《塔克拉玛干掠影》、刘锡津的《靺鞨组曲》、刘湲的《维吾尔音诗》、郭文景的《滇西土风三首》、唐建平的《后土》、刘长远的《抒情变奏曲》、赵季平的《古槐寻根》、顾冠仁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荣获经典作品奖。
颁奖仪式后,彭家鹏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张国勇指挥中央民族乐团演奏了12部获奖作品的精彩乐章。这些动人心弦的民族乐曲让人开阔视野,一饱耳福。6月7日至9日,首届“华乐论坛”在河北廊坊举行,与会专家把交流的核心放在了对12首获奖作品和民族管弦乐创作的研讨上。
现 状
势头良好 风格多样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管弦乐艺术有了飞速的发展,乐队编制的完善,乐器制作技术的提高,特别是乐队演奏员演奏技艺及素养的提高,为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也为作曲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发挥的余地,吸引了更多作曲家加入到这一艺术品种的创作中来,民族管弦乐创作的势头是良好的、可喜的。
作曲家唐建平介绍了自己创作《后土》三个方面的音乐线索:“一、用乐队浓重的低音和各类非常规的音响象征厚重的大地和大自然的声音。二、在上述背景上,以模仿远古骨笛的笛声为先导,并在音乐的每一重要段落处分别用埙、葫芦笙、巴乌等有特色的中国管乐器,引导音乐作连贯性发展和变化。三、引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彝族打歌、撒尼族姑娘的情歌和祭祀地母的歌曲以及彝族海菜腔四首民歌录音,拓展了过去用民歌曲调改编创作的方式,让民歌作为音乐结构中的重要材料担负音乐发展推进作用并表达明确的音乐意义。”
《岁寒三友——松、竹、梅》是作曲家顾冠仁考虑已久的创作题材之一。他说,“劲松”这一主题先由中音笙奏出,后由乐队奏出,开阔的节奏、大音程跳进的旋律以及强烈的音响对比,表现了松的挺拔、坚韧;“翠竹”这一乐章我抓住竹的飘逸而有韧性、直竿亮节这些特性、气质,在弹拨乐器奏出的飘逸、流动的伴奏音型的衬托下,用梆笛清脆明亮的音色演奏出舒展而充满活力的主题;“腊梅”则基本上以古琴曲《梅花三弄》作为创作素材。
为了提高艺术性,作曲家刘长远特别注重把民族音乐风格与当代作曲技法有机的结合,“《抒情变奏曲》的主题是原创的,但主题借鉴了我国南方民间小调的风格,因此决定了作品的中国音乐特色。因为巧妙地运用当代的很多作曲技术,使音乐脱离了过去习惯的俗气写法。音乐中还时常出现多调式、多调性、无调性的音乐片断。”
音乐理论家李西安、赵冬梅则对谭盾的《西北组曲》十分赞赏,“在《西北组曲》中,作曲家大量应用了具有浓郁西北地方风格的音乐素材。除了对民歌主题的直接引用,对民歌主题进行较大幅度的加工也是这部作品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重要手法之一。”
音乐评论家刘再生认为:“中国传统乐器的音色,多具独特个性而欠缺于共性的组合。金湘在民族管弦乐作品音色处理方面,扬其长而避其短,具有调动民乐音色美感的奇异独特的高超手法。金湘调配的音色,或者突出高音笙、笛和浓重的低音革胡、低胡两种极端音色;或者强调某一种乐器及其声部独有的音色美特征;或者以固定的节奏音型用板鼓、定音鼓、排鼓敲击鼓边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特殊节奏音色印象。”
正如音乐理论家乔建中所说,从上世纪60年代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随想》开始,就有专业作曲家介入到民族音乐创作中来,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一方面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带来了很多启示——作曲家能关心这门艺术,这门艺术会有很大改观。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专业作曲家开始关注这个领域,这一关注就带来了合奏艺术和独奏艺术的发展。大型协奏曲、幻想曲等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时期,全面推动了20世纪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的进程。目前,民族管弦乐创作进入了作曲家创作个性化的时代,个性化才能多元化。作曲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自己对艺术的体验,用自己的创作语汇进行创作。
未 来
扎根民间 眼睛向下
虽然现在的民族管弦乐创作的环境非常好,不是写出来作品没人演,而很多时候都是乐团在等“米”下锅,但与会专家并没有盲目乐观,他们更多地关注到了民族管弦乐创作的一些“软肋”。
“作曲家对传统音乐的深度介入不够,刘文金创作《长城随想》酝酿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环境触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但他冷静下来开始写作时发现自己在音乐学院学习的那些东西不够了,于是自己私底下下功夫,去学习说唱、戏曲、民歌……最后找到了很多。巴托克从1930年到1936年,一边创作一边收集民间音乐,他一个人记下的民歌就有30000多首,我们哪一个作曲家下过这样的功夫?现在还处于我想写什么就去找什么,而不是全面地建设自己的创作基底。另外我认为还要有很好的技术、技法。技术、艺术、生活、创作,这些决定了作曲家作品对观众耳朵的冲击度。希望作曲家在创作的同时对中国传统音乐有更多了解、更多积累、更多长期静下心来的学习,到民间去、眼睛向下。”乔建中由衷地说。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王建民则建议作曲家写一个东西要真正狠狠地“扎”进去,他表示,“写作过程中应该与演奏家有更多的接触,不要有自己的架子,应该更加注意民族音乐‘语法’问题。上海音乐学院有全国惟一的民族音乐作曲专业,孩子们写作民族音乐的兴趣越来越高,虽然报名人数每年呈上升趋势,但民乐作曲专业还是‘矮’一头。其实作曲系的学生应该都学习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专业作曲家要更深入、自觉地了解中国民族乐器的性能、音色、音质”,这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驻会副主席、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伟最大的期待。
此外,与会专家还为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由于绝大部分民族管弦乐的创作者在内地,台湾著名指挥家陈澄雄和香港新声音乐协会主席兼艺术总监邱少彬建议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一个资料库,“我们跟许多作曲家没有来往、不认识,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们的作品呢?演出了人家的作品版权费又到哪里去付呢?这个资料库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著名指挥家卞祖善则提议:“筹建一个华乐创作基地,为作曲家提供条件,使其能潜心为华乐谱写能留下来的曲子。”
(编辑:孙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