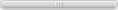自传体式影像书写的继续——电影《我11》观后
同《青红》一样,《我11》中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电影在很多方面都打上了王小帅的痕迹。
首先,符号化的物的表意。王小帅通常喜欢用具体的物件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来表达残酷的青春物语,比如《十七岁的单车》中的自行车,《青红》里的红色高跟鞋,《我11》中的白衬衫,都是作为关键符号出现在影像中。自行车、红舞鞋、白衬衫、都是与青春、少年、美好的希望结合在一起。但是王小帅的影片中却将这一系列符号同青春的阵痛、乃至死亡联系在一起。
王小帅电影中原本应该象征着美好、青春、甚至爱情的物件却都是以一种被撕碎的方式呈现在影像之中的。这些物都有过同样的经历:阶段性的丢失。无论是《十七岁的单车》中阿贵那辆被偷窃的自行车,还是青红那双被扔了的红色高跟鞋,还是王憨的珍贵的白衬衫。这些对于主人公而言非常珍贵的物件,却都遭遇过阶段性的丢失。这种丢失的经历通常都会与一个事件联系起来,这个事件背后会有一种深刻的阵痛。《我11》中的白衬衫是一个关键符号,整个故事是围绕白衬衫的一个事件展开。由“想要白衬衫——被拒绝——获得白衬衫——白衬衫丢失——白衬衫找回”为叙事线索,零散的个体感悟式的碎片记忆由这个事件串联起来。从这个层面上说来,《我11》承接了《十七岁单车》的叙事模式。在“白衬衫”这个事件背后,还安置了一个谢家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作为一个暗线的形式存在的,轻描淡写般隐藏在王憨的成长记忆里,若隐若现。通过觉强和王憨这两个人的偶遇将这两条线串起来,觉红就是另一个青红,白衬衫让觉强和王憨相遇,也让王憨的成长和觉红的悲剧有了交集。在《我11》的主线之外呼应了青红的故事,同时隐隐绰绰地加入很多说明性旁白,以达到一种对青春残酷物语的表达。王憨本来珍爱至极的白衬衫被沾染了鲜血,这让儿童王憨直视最残酷的死亡,以一种极度生硬的方式催化着王憨的成长,以近乎残忍的方式结束了王憨的童年。这里可能被人忽视的一点是,白衬衫上所沾染的血是属于觉强的,觉强是一个杀人犯,但他也是一个少年,他的死亡同样也是惨烈的。王小帅电影中所有和青春、美好有关的物作为关键符号都完成的是一种青春残酷物语的表意。
其次,主观化的表达。从《青红》开始,王小帅似乎就想要将一种去政治化、更为主观化的眼光去体察特定的“文革”末期的大时代。王憨似乎看到了历史,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政治事件只是构成了他的生活背景却远非他们的生活主题。《我11》中,这个视点已经被主观化到王憨那里,这种冷漠表现得更为明显。《我11》中关键的场合,王憨都无一例外的身在现场。然而王憨作为一个孩子,他所做的只能是在现场作为一个记录者或者说一个视点记录下来罢了,王憨的角色更多的像一个缺席摄像师的摄像机,它只是单纯的摆在那里,没有自己主观的好坏善恶评判,他只是事件或者历史的记录者,却不再是历史的参与者。《我11》片中有个相对准确的一幕:小孩子玩游戏,听到大人围坐着有说有笑,他们似乎在谈论着什么东西却又有难言之隐。他听得很完整,但却是在无意中听到的,其他事情,当真不如一件白衬衫来得重要。
最后,影像背后都有一种深层的反思与关怀。两部电影都是以广播体操的口号声将观众拉入影像中的历史记忆,广播体操作为标准化的身体的规训,本身也就隐喻了特定的时代在身体上的规训。而同样的,还有那种广播式的录音机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这种节目体现的特定时代对思想上的规训。无论是青红的父亲、觉红的父亲、还是王憨的父亲、他们都是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知识分子。面对精神或者文化极度匮乏的山区,他们的困惑与痛苦不言而喻。青红的父亲唯一的动力是让青红考回上海,上海已经作为一个符号成为文明、现代、好的社会的期许。而王憨的父亲也是在不遗余力地教王憨有关印象派绘画的东西,他们都想要摆脱一种制度化的规训,都极度渴望知识、文明、自由。《青红》和《我11》展现了在那个混乱的、激进的血雨腥风的时代,知识分子以一种卑微的方式存在着。但是他们存在的卑微并不代表着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斗争他们的反抗恰恰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不竭的动力。
(编辑:孙育田)